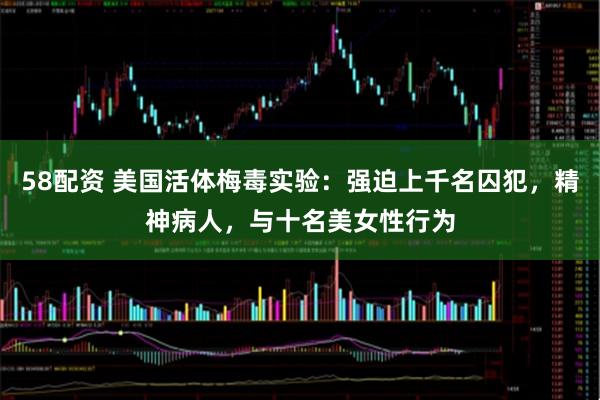
说起美国在二战后的那些医疗研究,你可能觉得是救死扶伤的英雄事迹,可有些项目一挖出来,就让人脊背发凉。
1946年到1948年,美国公共卫生局在美国境外搞了个梅毒实验,地点选在危地马拉,直接针对当地弱势人群。
领导这个项目的家伙叫约翰·查尔斯·卡特勒,他是个医生,早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,1941年拿到医学博士学位,之后就进了公共卫生局,从事传染病控制。
卡特勒之前参与过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监狱的淋病实验,那时候他就习惯用囚犯做活体测试。现在,他把这套玩法带到危地马拉,名义上是研究梅毒传播和治疗效果,实际上就是拿人命当耗材。
展开剩余85%为什么选危地马拉?简单,因为那时候美国影响力大,当地政府容易合作。公共卫生局跟危地马拉卫生部、劳工部等部门搭上线,项目资金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。
卡特勒带队,团队里有美国医生、实验室技师,还有当地助手。他们目标直指梅毒、淋病和软下疳这些性病,当时二战刚结束,美军士兵染病成灾,欧洲战场上就有七八万士兵中招,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一年内四分之一感染。
政府急着找廉价办法控制传播,但国内舆论敏感,就把实验场子挪到国外。结果,危地马拉成了试验田,受害者主要是穷苦的本土居民和印第安人。
实验规模不小,总共牵扯到5500多人,其中至少1308人被故意感染。对象包括军队士兵、监狱犯人、精神病院病人、妓女、孤儿,甚至麻风病人和农村小孩。
士兵占大头,大概600人,因为他们被视为高风险群体。监狱里关的上千人,基本是轻罪犯人,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。
精神病院的患者有300多个,多是慢性精神障碍者,被锁在机构里没人管。妓女选了十几个,从城里街区拉来,先用金钱诱导,然后强制染病。
孤儿和学校小孩也卷入后期血清测试,年纪小的才10岁。卡特勒他们挑这些人的理由很简单:这些人社会地位低,声音小,不会闹出国际风波,还好控制。
感染方式五花八门,先试了最“自然”的,通过妓女传播。团队从兔子身上培养梅毒螺旋体,给妓女注射或直接暴露,让她们跟士兵或囚犯发生关系。
起初效果慢,因为传播率不高,后来卡特勒改成直接下手:用针头从手臂或颈静脉注射病毒溶液,或者在生殖器、胳膊、脸上刮破皮肤后滴上细菌悬浮液。
最狠的是脊柱穿刺,直接把螺旋体打进脊髓,模拟晚期神经梅毒。淋病和软下疳也类似,用脓液或培养菌抹伤口。整个过程没征得任何人同意,参与者被骗说这是“疫苗”或“免费体检”。
卡特勒团队每天抽血、做腰椎穿刺,采集样本寄回美国实验室分析螺旋体数量和抗体反应。有些人分到治疗组,用青霉素或砷剂测试疗效,但大多数是对照组,啥都不给,就眼睁睁看着病变重。
你知道吗,这时候纽伦堡医生审判已经在1946年开庭,美国人明明知道人体实验的底线,可卡特勒他们照样干。项目从1946年夏启动,卡特勒亲自坐镇危地马拉城郊实验室,监督每个步骤。
1947年高峰期,感染高峰,团队记录症状进展:从发烧、皮疹,到溃疡、皮肤脱落,再到神经损害和心血管问题。监狱和病院成了数据工厂,医生们用表格列出每日体温和死亡率,笔迹一丝不苟。
实验本该6到8个月结束,但拖到1948年,因为资金跟上,合作方催着出成果。同期,美国国内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还在继续,那是从1932年开始的黑人患者观察项目,卡特勒也掺和过后期阶段。两个项目一脉相承,都是无视伦理,拿穷人当小白鼠。
为什么这么干?表面上看是为军队找性病防控方案,实际是学术野心。卡特勒想搞清梅毒自然史和青霉素最佳剂量,当时青霉素刚证明有效,但传播机制不清楚。
他在报告里强调“高浓度注射能模拟重症”,还测试不同体位和接触时间的感染率。团队没发表过正式论文,数据散在私人笔记和华盛顿档案里。
1948年项目收摊,资金断了,卡特勒打包设备回国,大部分感染者扔那儿不管。只有700人左右勉强拿到些治疗,但治愈率低,许多人带病出院,病毒传给家人。
官方记录到1953年有83人死于并发症,像败血症或心脏炎,但没明确归因实验。后期到1953年,他们还继续血清学调查,抽取更多样本,包括从孤儿院和乡村学校。
卡特勒呢?项目后他升官发财,1949年去印度领WHO项目,1958年当助理卫生局长,1960年进匹兹堡大学当教授,教流行病学到退休。2003年他87岁在美国去世,档案封存国家档案馆。表面风光,实际手上沾满血。
其他涉事人像托马斯·帕兰,美国卫生局长,当时批准项目;约翰·马奥尼,实验室主任,提供细菌样本;还有当地官员胡安·玛利亚·富内斯,帮着协调监狱。这些人没一个站出来认错,档案曝光前都当没事人。
尘封60多年,直到2005年历史学家苏珊·雷弗比翻卡特勒旧文件,才炸锅。她在研究塔斯基吉时顺带挖出这个,2010年10月1日公开发表。
消息一出,国际哗然,美国政府赶紧灭火。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给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·科尔博姆,道歉说这是“可耻行为,不代表美国价值观”。希拉里·克林顿和卫生部长凯瑟琳·塞贝利乌斯也公开认错,承诺调查。
11月,奥巴马成立生物伦理问题总统委员会,2011年9月出报告《伦理上不可能:1946-1948年危地马拉性病研究》,直指这是“严重伦理违规”,即使按当时标准也站不住脚。报告详列了感染细节、死亡数据,还对比纽伦堡准则,强调知情同意和最小伤害原则。
道歉有用吗?受害者家属不买账。危地马拉人起诉美国政府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,案子像曼努埃尔·古迪尔·加西亚诉凯瑟琳·塞贝利乌斯,2012年开庭,但全被驳回。
理由是主权豁免和时效过长。到2017年,没一分补偿落地,只有些医疗援助基金,帮后代检查遗传梅毒。许多家庭散了,疤痕代代传。报告还挖出实验样本用到1957年,美国实验室用危地马拉血清配疫苗,这更添讽刺。
回看这事,根子在权力失衡。美国战后自信爆棚,以“公共卫生援助”名义伸手境外,实际就是殖民遗毒。危地马拉那年正值独裁时代,乌比科政权上台,社会底层更惨。
实验不只毁了1300人,还污染社区,梅毒病例几年内翻倍。卡特勒他们没想后果,只顾数据,报告里冷冰冰列数字,像“感染率达89%”。
这跟塔斯基吉一比,后者至少没故意感染,前者直接下毒手。两者都暴露美国医疗体系的双标:对本国少数族裔是观察,对外国穷人是实验。
结语:总的,这事告诉我们,科学无国界,但伦理有底线。卡特勒们以为数据永恒,实际留下的,是几代人的痛。
发布于:河南省大牛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